2017年6月23日 周五
牛津 晴

几年前,我拿出老爸几幅习作为蒲公英农民工学校募款。梵志捐了两万,挑了幅素描。收到原作后,他说了句:“画得好啊,我赚了!”
昨外出晚餐,老地方遇到几位流浪者。读过一份非政府机构的报告,其中提到英国流浪人口,一小部分已是永久状态。他们不回家,也拒绝入住慈善机构或政府提供的住宿点,漂泊一生。如何在街头帮到他们,在我家并无共识。我的做法最简单,就近给他们买个快餐,比如麦当劳、肯德基。若没时间,就放点零钱走人。我承认,这样做既让他们饱餐一顿,更为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妻子的做法是买好食品送他们,多半也是快餐。底线是不给钱,怕他们买烟或大麻。常驻北京时,我们住东三环。某晚散步,一对青年男女上前求助,说是丢了身份证,无法找工作,住不了酒店,也没饭钱,当晚要赶回A省老家。我们领他俩到附近超市买吃的,他们很挑剔。买了吃的,又说要打车费,还有南站住宿费,才察觉上当。每次被骗当然郁闷,但以世上无家可归者总比骗子多聊以自慰。儿子的处理,则完全不同。他的理论是,既然行善,就得给对方选择权,给他们现金,让他们自由支配别人的好意,可买食物,也可买烟抽。他的假设,一个麦当劳套餐,大概能抵御3—4小时饥饿,一包便宜的20支香烟可抗饥饿一整天。我无法判断此说有无科学依据,至少他信。
不过,Tommy的自信,于我并不都是好消息。他的风险偏好远远超出我心脏的承受度,中学时,他是校橄榄球队的边锋,以速度见长,但体重吨位差些,重伤多次,肩胛内已打上数枚钢钉。上大学时,他喜欢上了蹦极。在香港大学交换时,他曾邀请我去澳门电视塔观礼,目击他从233米的亚洲第一高蹦极跳下,我谢绝了。从现场录像看,他是背对着一跃而下的,背景里是一群日本少女的刺耳尖叫。更要命的是,某日正在非洲远足的他发来邮件,说正在津巴布韦,少有的主动联络,心想一定是钱包空了,或者被偷了,需要货币增援。他说,他边旅行,边勤工俭学,钱没问题,想告诉我的是,订了维多利亚瀑布的世界第三高蹦极点,高度111米,从一座铁桥上下落。我回复,跳完就好。他补充说,还没跳,是明天。我悲愤交加,问他为何要在跳之前通知我?!(我一般不用惊叹号)不残酷吗?
中午坐大巴到伦敦。先去唐人街午餐,虾仁云吞面。拐进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伦敦交通博物馆。住伦敦多年,从没进去过。伦敦地铁建于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上海第一条地铁线通车已在一个多世纪后,远比祖师爷伦敦摩登、宽敞,但没伦敦注重细节与品位,比如巴掌大小的伦敦地铁图,像发行邮票一样,每隔一季度有新款设计,附上更新信息。一个城市是否宜居、优雅,多在不起眼的细节中。不期而遇的小惊喜,其愉悦足以支撑一天的劳作。
手工艺区,有个木工摊位,我被一个原木的红苹果吸引了。年轻的摊主说,红苹果是老爸在家里作坊做的,先选对纹理对路的上好原木,用车床一层层刨去,木纹自上而下,漆色也恰到好处,活脱一个真苹果,爱不释手。价格不贵,15英镑,想买下,可惜没带现金,摊主不收信用卡,作罢。
下一站直奔皮卡迪利的皇家艺术学院(RA,Royal Academy of Art),今天是“伦敦印刷品原件年展”(“London Original Prints Fair”)闭幕日。中国毕昇的印刷术比西方早400年,但近代印刷文明的里程碑还得从德国金匠古登堡开始。大部分陈列的展品都明码标价,来自英国、欧美50多个收藏机构、画廊和印刷工坊。展品中有伦勃朗、马蒂斯、惠斯勒、毕加索、霍克尼等名家的版画精品。印刷术改变了我们对文明的存在感,也改变了承载文明与思想的介质,并使大众传播成为可能。没有印刷品,人类的近代史将无从呈现。展览中,有一幅苏维埃早期的宣传画,“A Worker Sweeping Criminals Out of the Soviet Land”(“把犯罪分子扫出苏维埃大地”),作者列别捷夫(Vladimir Lebedev),一位从沙皇晚期过渡到苏维埃新政权的新潮画家、视觉艺术家、漫画家、插画家、结构主义的实践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苏维埃“动员和宣传部”(Agitprop)专门设计宣传画。画面上,米色的背景,一位身着蓝色时髦工装的工人,正用扫帚把三个五颜六色的坏分子从他脚边赶走。不像工人,扫帚的头是红的,把是黄的,坏人体态卡通可爱,色彩与表达完全没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残留温情与浪漫。列别捷夫1891年生于彼得堡,赶上沙皇时代的尾巴。新政权建立后,深谙宣传的列宁急需艺术家为新政权服务,一代艺术家面临人生与艺术的突变,音乐、艺术、戏剧、文学、电影、诗歌:马雅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叶赛宁、阿赫玛托娃,都在革命的漩涡中兴奋、挣扎,以求新生。
看到列别捷夫的画,我想到友人、画家曾梵志。100年前,列别捷夫这一代画家抖落沙皇时代的余烬,转身到了列宁的革命画室,没有选择。40年前,梵志这辈学画青年开始从人体和人性学起。他进美院读书,前后考了三年。这几年,我常去他北京望京的工作室做客。梵志的话不多,在画室,说话更少。他抽雪茄,我喝茶。我最放松的,是做一个隐身人,坐在地上看他作画。关上画室的门,他就把外面的世界彻底隔断了。他享受画布、颜料的庇护。外面,是面具世界。他不喜欢面具,但不得不无奈接受,故创作了“面具”系列。不过,令他深恶痛绝的“面具”成就了他的艺术和国际名声。这个带有自传式忏悔的系列,面具几乎成了他的标志。他痛恨标签。近10年,即便买画的订单不断,拍卖价格高居不下,他拒绝再画任何“面具”。2014年,巴黎罗浮宫邀他以德拉克洛瓦名作《自由引导人民》为母题创作一幅作品,并一起陈列。那阵子我常去他画室,一坐就是半天。为了这个展,他画了三幅,都是两米乘六米的大作品,画室内搭了高高的脚手架,油画颜料都用大脸盆调兑。当他用拖把大小的画笔往画布上涂抹色块时,我开始体验画家强劳力的一面。过了几天,又去看画。他臂膀已抬不起来,只能歇了。他画室里,有不少他的早期作品。他告诉我,他最在意的是他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作品《忧郁的人》。1992年,穷困潦倒的他以500元卖了出去。不过他一直念叨那幅画的下落。20年后,该画又露面,他以1000万人民币将它买回。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再画一幅?他叹口气说,绝对画不出,那个感觉没了。
大英帝国的历史虽与中华不在一个量表上,但因其博物观念与收藏癖,短短五百年,俨然已成“文明古国”。英人对考古、文物、珍玩与艺术品的痴迷,常令我感叹。大英博物馆、V&A(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重要特展,门票多半在开幕前三个月订完,甚至得提前半年预订。1973年,大英博物馆有中国出土文物展,这是中国出土文物首次在西方国家展出,由泰晤士报集团筹办。当时,中英刚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之前是代办级)。有记载,所有门票提前9个月订购一空,成为当年的文化事件。一国一城,对艺术最重要的激励来自有品位的观众。
大英博物馆现有藏品600万件,其中中国珍藏2万多件。1990年代初,某天去大英博物馆。一个展厅入口,放了一个中国周朝的青铜大鼎,有半人高,鼎口覆有一块有机玻璃,中间有孔,观众可投币入鼎,为博物馆募款。我觉不妥,留言请大英博物馆停止这种做法,尊重中华宝物。半年后再去,鼎已不在,应该是物归其所了。
我就读的莱斯特大学,有个国际知名的博物馆系。友人、台湾同学张誉滕当时就在那里读博士,后来出任台湾自然博物馆馆长。他的博士论文有关罗伯特·郇和(RobertSwinhoe,1836—1877)。此公是19世纪英国博物运动的重要人物。1861年至1866年间,他曾两次到台湾,任驻打狗(现高雄)副领事,但他“不务正业”,几乎把所有时间用于收集动物特别是鸟类标本,完成了“台湾鸟兽类”的编目。台湾现有鸟种,三分之一以上是他首先发现并公之于世的,被誉为东方鸟类学之父。在外交官和博物学家两个身份中,他用外交官职务之便,成就了鸟类学家的抱负。高雄打狗山上,还有当年英国领事馆的红砖官邸。沿古老步道下山,郇和蜡像坐在山石上,穿着野外装,身旁蹲着几只好奇的山猴。当时,走动最多的台湾同学还有现任政大传播学院教授冯建三、荣休教授罗文辉。后来建三介绍我与在伦敦大学读博士的郭力昕相识,都成了对岸的挚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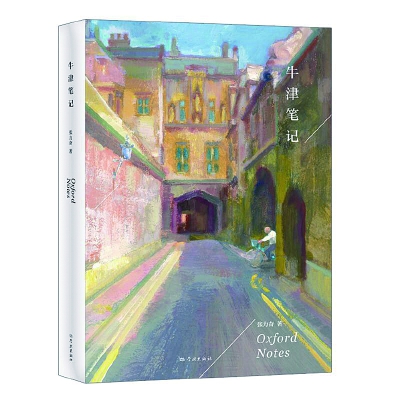
《牛津笔记》
张力奋 著
学林出版社

席地而坐的为本文作者
本书以日记体的方式结构全篇,从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7年6月24日,每篇日记配备了一幅作者在牛津拍摄的黑白照片。作者用直白的文字和珍贵的黑白影像记录了其在牛津大学客座一学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书中,作者谈时局,谈生活,谈典故,谈童年,表达了对西方知识领域的思考和对人文价值的关怀。可以说,本书是他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是英式essay与中式小品的曼妙结合。
[作者简介]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校任教。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副主编、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FT睿》杂志创刊总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新闻主编。曾获亚洲新闻奖等国际奖项。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校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著有《世纪末的流浪》(合著)、《黑白灰》、《历史的底稿》、《中国领导力》(合编)等。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