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7日 周一
伦敦 晴

1727年,物理学家牛顿去世。这具遗容石膏像现存爱丁堡大学,近代医学重镇之一。爱丁堡颅相学会有2000多个面容石膏像收藏。信托人规定,即便科学冒犯了民意,也绝不允许遣散或销毁这些收藏。
几声风笛飘来,提醒我,要告别爱丁堡了。据说风笛源于中东。不过我记忆中,她只属于苏格兰高地的旷野风啸。音色像中国唢呐,高亢如军乐出征,嘹亮得如同金属的光泽,哀婉时也可呼天抢地。风笛的气囊如肺,靠簧管振动发声。音乐的记忆,多半与第一次听到它时的场景有关。二十多年前,去苏格兰佛特威廉的黄昏途中,远处风笛声,若有若无,掠过莽原。风笛就此与苏格兰绑定终身。人生,单行街上的旅行,一站站向前,月台上相逢与离别。跋涉久了,或对人世间漠然,或心生感恩。
离开爱丁堡前,突然有种莫名的冲动,想去老城的皇家英里大道(Royal Miles),看一眼站在那里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没有特别的理由。两尊青铜雕像,立于老街两侧,相隔数十米。高等法院门口,是休谟,披着罗马袍,坐在高昂的基石上,骑士般潇洒,脚背裸露,已被旅客摸得发亮,手握巨书,低眉沉思中。亚当·斯密,他站着,左手挽在胸前,上身前倾,似乎在与人辩论。太阳逆光刺目,把斯密的面目打得模糊,只留下轮廓的光晕。这两位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巨子,早年就惺惺相惜。斯密终身未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体弱多病,早早把后事托付给休谟,特别是身后受理他的遗著。未料1776年休谟先亡,斯密为他送葬。发表《国富论》后,这位伦理学教授令英国和欧洲知识界疯狂,用他“看不见的手”摘得经济学鼻祖的桂冠。他的“有限政府”学说,开始驯化利维坦。18世纪的苏格兰,有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双城记,是新思想的麦加,甚至比伦敦前卫,如哲学、法学和医学。格拉斯哥大学奠定了近代临床医学、解剖学的基石。苏格兰思想启蒙运动,一时天才成群出现。除了斯密、休谟,还有弗格森、里德。
前几天,应邀去爱丁堡大学讲演,题目是《社交媒体与中国日常生活》。近百位听众中,多半是爱丁堡当地的教授、政府官员、商人、学生,也有听众从斯特灵远道赶来。苏格兰与中国有些缘分。19世纪中叶,中国新闻之父、改良派思想家王韬为逃避清政府通缉,曾辗转到苏格兰避难多年。19世纪下半叶,辜鸿铭曾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就是爱丁堡人,据说溥仪的英语也带丁点苏格兰口音。
我问听众,谁使用中国的微信,居然哗哗举起一片手臂,目测至少有六成。为记录这一意外的发现,我只得请听众帮忙,再举一次手,让我拍照留存。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民间热衷东方的中国茶、丝绸、瓷器和皇家园林,现在轮到腾讯的微信。
前天,我由贝尔法斯特飞回爱丁堡。起飞时已入夜,青紫的云层,裹住万家灯火。这是我第一次去北爱尔兰,大不列颠王国(United Kingdom)最敏感的一块疆土。走在福斯路(Falls Road)上,我有片刻的幻觉。这条长达1600米的街道,曾是BBC新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路名之一。北爱尔兰血腥冲突中,它是天主教社区的精神圣地。他们决意脱离英国,追求共和,捍卫爱尔兰独立。一街之隔,是另一条举世闻名的街道——尚基尔路(Shankill Road),新教社区的堡垒,忠于女王和大英王国。1968年,北爱尔兰局势恶化,简称“The Trouble”。接踵之间,两条街道成为对抗、恐怖和血腥的代名词。
沿街,有块墓地。背靠的高墙上,一幅蒙面枪手的巨幅壁画,斑驳褪色。一位老头,精瘦骨感,正埋头清扫墓碑。墓园中的花草,因为背阴,凋零得快,闻得见残花的死气。我上前跟老人打招呼,他没正面搭理,只是浅浅抬抬头,手指戳了戳墓碑,愤愤地说:“他们死得太年轻。我守了一辈子墓,也老了。”他表情有些变形,眼窝深陷,满是悲愤和无奈。北爱尔兰停火了,重获和平,他却失去了战场以及生存的意义。他为爱尔兰独立而战,一生定格在这条街道上。我问他,去过隔壁的尚基尔路吗?他尴尬一笑,说去过几次,夜间偷偷进去的。90年代中叶,我刚到BBC工作,正是北爱冲突最恐怖的岁月。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爆炸、暗杀事件频频,同时殃及伦敦,时间久了司空见惯,以致麻木。死亡只是新闻中的数字游戏。
那年头,记者到贝尔法斯特采访,视为战地。代表爱尔兰共和军的新芬党,成了撒切尔政府的死敌。其党魁是灰白胡子的亚当斯(Gerry Adams),经常在BBC新闻中露脸,抨击英国政府。唐宁街10号极为恼怒,撒切尔把新芬党的媒体曝光称作“暴力的氧气”,但碍于言论自由,无法对新芬党禁言。最后英国最高法院作出一个黑色幽默的裁决:对亚当斯的所有采访,无论电视广播,必须由第三者配音,可见其人,不可闻其声。亚当斯养活了一批靠他为生的配音人。与形象相比,政治家们似乎对自己的声音更在乎,更敏感。撒切尔夫人上任后,专门请了声音教练,让她的高音变得柔和、亲民些。1998年,“星期五和平协议”签署,北爱终告停火,人们重新听到久违的亚当斯低沉的原声。
正如历史上的帝王宫殿、古堡和墓葬日后成为人类文明的奇观,当年北爱敌对社区的隔离带,现在已是游客必到的景点。停火已近20年,仍有1300起谋杀尚未结案。今人不知,20世纪初,贝尔法斯特已是繁华且有品位的欧洲都市,造船业鼎盛一时。1912年“泰坦尼克号”就在此下水。后来,宗教暴力与疯狂渐渐毁了这个城市,将其推向血腥。临行,我赶了个早,沿着拉甘河散步。贝城仍在睡眠中。太阳刚露脸,河面如镜,晃耀金色波光,漫射开来。岸边红砖墙下,有零星的晨跑者,享受失而复得的和平。
回到伦敦家中。回国后,房子一直空着。跟宠物一样,房子得养。主人不在,房子会失落,坏得也快。前年,我将多年的藏书从伦敦海运上海,近70箱。运抵复旦大学时,搬家公司告诉我,重量近3吨。书架不够,只能临时找库房安置。书是读书人的十字架,背上了就很难卸下。伦敦的书没完全搬空,留了些。走道、窗台、洗手间、楼梯角落,东一摞、西一摞,像撒狗粮。有书在,感觉安全些。随手抽出一本,翻几页,也是满足。
一早,去家边上的公园散步。晨雾已升起,停在齐腰的半空,不往上走。一见太阳,刹那间就散了。地平线远处,三三两两的遛狗人,慢慢变大。他们多半是被狗儿女拽出被窝的。共处久了,狗越来越像主人,除了性情,有时面相也越来越近。主人善,狗多半也善。主人心急,狗也暴躁。主人害羞,狗也不擅搭讪社交。对狗,英国人通常很友爱,有时比对自己的同类还仁厚。一位老太太推着婴儿车走近。婴儿车里,端坐着一条狗,耷拉着头。老太太解释说,狗儿已上岁数,患类风湿关节炎,已恶化,跑不动了,只能用婴儿车推它外出溜达。若它情绪好,愿意下车,就走几步,不乐意,就坐着兜风。这些年,我至少向数百个狗主人请教过狗的品种、身世、脾性,听过真实或明显涉嫌美化的狗故事。英国人热衷谈论的日常话题有天气,还有狗。对天气,他们是宿命论者,深知无力掌控,索性就停留在谈论的美学层面,至少没什么后果。对狗,英人有真实的生命体验。聊狗对英语颇有长进,妻子在中学、大学被迫学俄语。初到英国,英语茫然。一天散步,她问一温婉的老妇人,您的狗什么种?老太郑重介绍:“She is a bitch!”妻子觉得耳熟,心想怎么骂街了。再向老太求证。老太太重复:“She is a bitch!”(她是条母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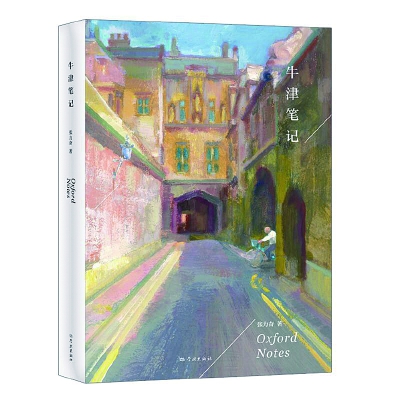
《牛津笔记》
张力奋 著
学林出版社

席地而坐的为本文作者
本书以日记体的方式结构全篇,从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7年6月24日,每篇日记配备了一幅作者在牛津拍摄的黑白照片。作者用直白的文字和珍贵的黑白影像记录了其在牛津大学客座一学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书中,作者谈时局,谈生活,谈典故,谈童年,表达了对西方知识领域的思考和对人文价值的关怀。可以说,本书是他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是英式essay与中式小品的曼妙结合。
[作者简介]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校任教。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副主编、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FT睿》杂志创刊总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新闻主编。曾获亚洲新闻奖等国际奖项。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校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著有《世纪末的流浪》(合著)、《黑白灰》、《历史的底稿》、《中国领导力》(合编)等。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